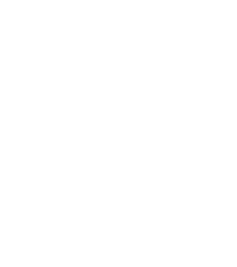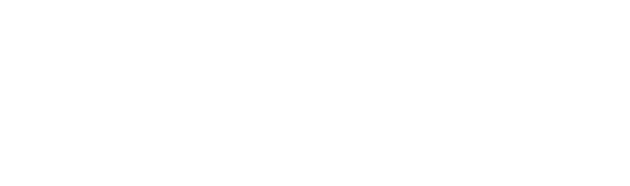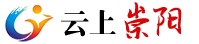作者:徐俊军
(三)
蝉鸣织织,声浪漫过原野。我站在田埂上放目远眺:金灿灿的稻穗在八月的烈焰中翻涌。千顷良田自脚下铺展成海,每粒谷壳都裹着阳光淬炼的金箔,随风起伏时泛起粼粼波光。远处黛青的山影被稻浪浸染,天地交接处浮动着碎金流淌的河川。白鹭掠过时带起一串穗浪,饱满的稻粒碰撞出沙沙细响,如同大地均匀地吐息,于是我张开双臂紧闭双眼,任稻香灌满衣袖……
十岁的暑假,照例是要下地干活的。生产队长说过,大一点的孩子都要参加双抢会战,一天可记两个工分。我数了数,这个暑假要是干满,能挣六十多个工分呢。
天还没大亮,队里的男女老少就扛着镰刀往田里走。我跟着徐婶,她是个干活的好手,镰刀在她手里像活了一样。我学着她的样子,左手拢住一把稻秆,右手挥镰,“唰”的一声,稻秆应声而断。起初还觉得新鲜,可没过多久,腰就开始发酸,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,滴在稻茬上。
“娃儿,歇会儿吧。”徐婶直起腰,用袖子擦了把汗。我摇摇头,继续弯腰割着。太阳越升越高,稻田里蒸腾起的热气让人喘不过气。我的手掌磨出了水泡,火辣辣地疼。但看着身后整齐的稻茬,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满足。
割下的稻子要捆成捆,一捆捆立在田里晾晒。男人们用扁担挑着稻捆往晒谷场送,沉重的担子压得扁担“吱呀”作响。我试着挑了一担,没走几步就踉跄起来,惹得大人们哈哈大笑。徐婶说:“等你再长两年,就能挑得动了。”
谷子进了仓库,转眼就要开始插秧。清晨,我跟着大伙儿去秧田扯秧。露水未干的秧苗青翠欲滴,带着泥土的芬芳。我蹲在田里,学着大人的样子,一手扶着秧苗,一手轻轻扯动。扯好的秧苗要扎成小把,整齐地码在箩筐里。
插秧是最热闹的时候。男人们赤着脚,裤腿高高挽起,在泥水里来回穿梭。女人们弯着腰,手指灵巧地将秧苗插入泥中。我也加入其中,虽然动作笨拙,但渐渐找到了节奏。泥水没过脚踝,凉丝丝地很舒服。偶尔有泥鳅从脚边滑过,引起一阵惊呼。
太阳西斜时,田里已经插满了嫩绿的秧苗。微风拂过,秧苗轻轻摇曳,像一片绿色的海洋。我站在田埂上,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,心里涌起一股自豪。虽然一天只能挣两个工分,但能为集体出一份力,感觉特别踏实。
傍晚收工,大家三三两两地往家走。徐婶从兜里掏出一个煮鸡蛋塞给我:“娃儿今天干得不错。”我推辞不过,接过来时发现鸡蛋还带着她的体温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,田埂上飘来阵阵混着泥土的气息,那是夏天特有的味道。
晚上躺在床上,浑身酸痛,却睡得格外香甜。梦里,我仿佛看见秧苗在风中摇曳,金黄的稻浪又翻滚起来;村民们在田间忙碌的身影。我知道,这样的日子还会继续,直到秋天,直到来年,年复一年。但此刻的我,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玩耍的孩子,而是能和大人们一起劳作的“小大人”了。
(四)
我的邻居叫牛爹,按辈分来讲要高我两辈,由于家穷,再加上长相丑,所以到了三十有六还没讨到老婆。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,好事媒婆帮他撮合了一门亲事,乐得牛爹嘴上笑开了花。
冬天来了,二场雪过后路上的积雪仍未消融,天气异常寒冷,北风突然转急,后山整片竹林应声摇晃,冰壳裂开的细纹沿着竹节蜿蜒,像无数条银蛇在苏醒游动,发出了古琴丝弦般的低吟;积雪压弯的竹梢不时甩落碎玉。这样的季节我们家不仅吃饭成问题,而且没柴烧也是个问题。
一个周末的下午,我见牛爹磨刀准备要到70里外的沙堆老山里面砍柴烧,于是我对母亲说:“妈,我也要和牛爹去砍柴。”
母亲看着我心痛地说:“外面的雪都还没融,莫去。”
我跟母亲软磨硬泡后,她最终同意了;那年我才十二岁半,也就是一九七三年。
天还没亮,鸡叫头遍的时候,我就被母亲摇醒了。灶屋里飘来红薯粥的香气,混合着柴火燃烧的烟味。我揉了揉眼睛,看见母亲正在往竹篮里装干粮——几个烤得焦黄的红薯,还有一壶热开水。
“快些吃,趁天没亮就得走。”母亲的声音沙哑而低沉。我捧着粗瓷碗,感受着热气在脸上蒸腾。灶膛里的火光映着母亲瘦黄的脸,那些皱纹像是被岁月刻下的沟壑,深深刻进她的皮肤里。
我穿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,背上竹篓。牛爹已经将斧头、麻绳都收拾妥当,正在往草鞋里塞干草。门一开,寒气就扑面而来,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。远处的山影还隐在黑暗中,只有近处的积雪泛着微弱的白光。
“跟紧些。”牛爹说着,迈开步子。积雪在脚下咯吱作响,我小跑着才能跟上他的步伐。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,远处的山峦显露出轮廓,像一幅水墨画。我的呼吸在空气中凝成白雾,睫毛上结了一层薄霜。
走了约莫两个时辰,太阳才懒洋洋地爬上山头。积雪反射着阳光,刺得人睁不开眼。我的草鞋已经被雪水浸透,脚趾冻得发麻。牛爹的背影像一座山,在雪地里稳稳地移动着。偶尔有积雪从树枝上滑落,发出“簌簌”的声响。
到了山里,牛爹选了一处向阳的坡地。这里的松树长得笔直,枝干粗壮。他放下工具,搓了搓冻僵的手,朝掌心哈了口气。“你捡些细柴,别走远了。”他叮嘱道,然后抡起斧头,开始砍树。
“咚、咚”的砍伐声在山谷里回荡。我一边捡拾枯枝,一边看着牛爹干活。他的动作很有节奏,每一下都精准地落在同一个位置。木屑飞溅,树身渐渐出现一道深深的缺口。突然,一阵风掠过树梢,积雪纷纷扬扬地洒下来,落在我的脖子里,凉得我打了个激灵。
正午时分,我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吃干粮。红薯已经凉了,硬邦邦的,但咬下去还是甜的。牛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,倒出几粒盐,让我就着红薯吃。“补力气。”他简短地说。阳光透过树枝斑驳地洒在地上,积雪开始融化,滴滴答答地落下来。
下午的活计更重了。牛爹将砍倒的树砍成段,我负责把树枝捆扎起来。手掌被粗糙的树皮磨得生疼,但我咬着牙没吭声。牛爹的棉袄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,在寒冷的空气中冒着热气。
等到收拾妥当准备下山时,日头已经西斜。我们每人挑着一担柴,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。我的肩膀被扁担压得生疼,但不敢喊累。牛爹走在前面,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。
走到半路,天色突然变了。北风呼啸着卷起地上的积雪,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。我的草鞋早就破了,索性脱下来光着脚走。积雪冰凉刺骨,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风越刮越大,卷起的雪粒打在脸上生疼。我的睫毛结了冰,视线变得模糊。
“把柴放下!”牛爹突然喊道。我还没反应过来,他就已经放下担子,快步走到我面前。他脱下自己的棉袄,不由分说地裹在我身上。“穿上!”他的声音不容置疑。我想要推辞,却被他严厉的眼神制止了。
风更大了,卷着雪粒在空中飞舞。牛爹只穿着一件单衣,却像感觉不到冷似的。他重新挑起担子,示意我跟上。我的眼眶发热,不知是被风雪吹的,还是因为别的什么。棉袄上还带着牛爹的体温,温暖着我冰凉的身体。
暮色四合时,我们终于看到了村口的灯光。那一点昏黄的光晕在风雪中显得格外温暖。我的脚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,但心里却涌起一股暖流。牛爹的背影在风雪中依然挺拔,像一座永远不会倒下的山。
回到家,母亲立刻生火烧水。他把我的脚按进温水里,用力搓揉。“疼……”我忍不住叫出声。“忍着。”她头也不抬,“不把寒气逼出来,明天就别想走路了。”灶膛里的火光映着他的侧脸,那些深深的皱纹里似乎藏着说不尽的故事。
那一夜,我睡得很沉。梦里,我又看见了那条雪路,看见了牛爹在风雪中挺直的背影。那个背影,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,也是我一生中最坚实的依靠。
多年后,每当我遇到困难时,总会想起那个风雪交加的傍晚。想起牛爹脱下棉袄裹在我身上的瞬间,想起他在风雪中挺直的背影。
那些记忆,就像冬日里的暖阳,永远温暖着我的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