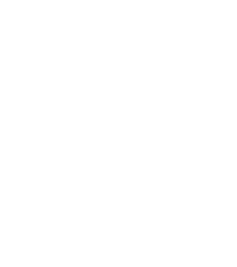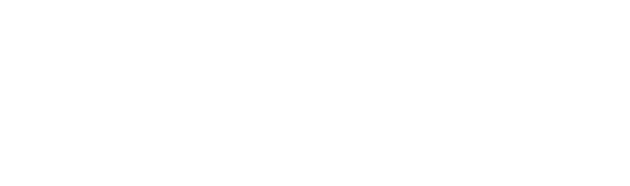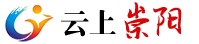作者:徐俊军
我的老家位于鄂南山区崇、通交界处的锁石村,因交通不便,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,这里土地贫瘠,有山无树,有水不落窝;要柴没柴烧、要水没水喝。一年到头为柴、米、油、水发愁。还有一个奇怪的是这里不但贫穷,连个地名都不好听,其名曰:尿婆塘。就是在这么个地方度过了我的童年——我家当时有兄妹七个,还有母亲和一个年迈的奶奶,共九口人靠着在县城工作的父亲每月三十五元的工资糊口。
(一)
天还没亮,我就听见灶房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。母亲又在摸黑生火了,她总是这样,趁着我们还没醒,先把一天的活计都安排妥当。我翻了个身,听见草垫子下面压着的稻草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
“三伢,别装睡了,快起来。”大哥的声音从头顶传来。我睁开眼,看见他正站在炕边穿衣服。大哥今年十五岁,他不喜欢读书,已经开始跟着生产队下地干活了。他的影子在昏暗的油灯下拉得老长,像一根细长的竹竿。
我揉着眼睛爬起来,看见二哥和老四已经在穿鞋了。老五(大妹)、老六(二妹)还在炕上赖着,七弟则蜷缩在角落里,像只小猫似的打着呼噜。母亲常说,七弟生下来时只有四斤重,跟只老鼠差不多大。
灶房里飘来红薯的香气,我咽了咽口水。每天早晨,母亲都会把前一天剩下的红薯切成薄片,放在锅里煎得焦黄。那是我们唯一的早餐,每人两片,不多不少。
“三伢,去把七伢叫醒。”母亲的声音从灶房传来,伴随着锅铲与铁锅碰撞的声响。我爬到七弟身边,轻轻推了推他。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,嘴角还挂着口水印。
我们七兄妹挤在堂屋的方桌前,像一群等待喂食的小鸟。母亲端着煎好的红薯片走过来,她的围裙上沾满了灶灰。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关节有些红肿,那是常年洗衣服留下的痕迹。
“快吃,吃完该上学的上学,该干活儿的干活儿。”母亲说着,又转身回到灶房。我知道,她又要开始准备猪食了。家里养了两头猪,那是我们过年时唯一的指望。
我小心地咬了一口红薯片,焦香的味道在嘴里化开。七弟吃得急,被烫得直吐舌头。二哥笑着把自己的水碗推给他,却被大哥瞪了一眼:“省着点喝,井水也不是白来的。”
吃完早饭,大哥带着二哥下地干活。我和老四、老五、老六背着母亲用碎布拼成的书包去上学。七弟还小,留在家里帮母亲喂猪。
学校在村东头,要走二里地。路上,我们经过王婶家的小卖部。橱窗里摆着花花绿绿的糖果,老六忍不住停下脚步,鼻子几乎贴在了玻璃上。
“快走,要迟到了。”我拽了拽老六的袖子。我知道老六在想什么,昨天她捡到了一分钱,足够买一颗水果糖。但她最后把钱交给了母亲,因为父亲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寄到。
教室里挤满了孩子,有的穿着打补丁的衣服,有的光着脚。李老师正在黑板上写字,粉笔灰纷纷扬扬地落下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,能看见远处的麦田。麦子已经抽穗了,在晨风中轻轻摇晃。
放学回家的路上,我们看见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从村口过来。四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:“是不是爹寄钱来了?”
我们跑回家,果然看见母亲手里捏着一个信封。她的手指有些发抖,小心翼翼地拆开。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十元钱,还有父亲的信。
“你爹说,这个月单位钱紧张,只能寄这么多了。”母亲的声音很轻,但我看见她的眼眶红了。她把钱仔细地折好,塞进围裙的暗袋里。
晚饭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,配着咸菜。大哥从地里带回一把野菜,母亲把它切碎了撒在糊糊里。七弟吃得津津有味,我却注意到母亲只喝了一小碗就说饱了。
夜里,我躺在炕上,听着兄弟们均匀的呼吸声。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,在地上画出一个光斑。我想起父亲上次回家时带来的那包水果糖,那是我们唯一一次尝到甜味。糖纸我还留着,夹在课本里,偶尔拿出来闻一闻,还能闻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甜香。
第二天是星期天,不用上学。天刚蒙蒙亮,大哥就把我们都叫醒了:“今天去捡麦穗,多捡点,过年就能吃上白面饺子了。”
我们拿着母亲用旧布缝成的袋子,和四个弟妹来到收割过的麦田。田里已经有不少人在弯腰捡拾了,大多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。
太阳渐渐升高,晒得后背发烫。我的腰酸得直不起来,手指也被麦茬划出了几道口子。七弟走不动了,坐在田埂上抹眼泪。我把自己的水壶递给他,又继续弯腰捡麦穗。
中午,母亲送来几个煮红薯。我们坐在树荫下分着吃,七弟累得睡着了,手里还攥着几根麦穗。我看着他瘦小的身子,突然想起母亲说过,七弟出生时差点没养活。那时候家里太穷,连买红糖的钱都没有,母亲只能喝凉水坐月子。
傍晚,我们背着沉甸甸的麦穗回家。母亲站在门口等我们,她的身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。看见我们回来,她连忙接过袋子,摸了摸我们的头。
“饿了吧?今天煮了稠一点的糊糊。”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我抬头看她,发现她的眼睛红红的。
晚上,我躺在炕上,浑身酸痛得睡不着。月光依旧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,在地上画出一个光斑。我听见母亲在灶房里轻声啜泣,还有大哥安慰她的声音。
“娘,别难过,等我再长大些,就能挣更多工分了。”
“你爹也不容易,在城里省吃俭用的.……”
我翻了个身,把脸埋在草垫子里。稻草的味道钻进鼻子,让我想起白天在麦田里的情景。七弟在睡梦中咂了咂嘴,似乎在回味那碗稠糊糊的味道。
第二天一早,我醒来时发现母亲的眼睛肿得像桃子。但她还是像往常一样,天没亮就起来生火做饭。灶房里飘来红薯的香气,和往常一样。
我们围坐在方桌前,每人面前放着两片煎得焦黄的红薯片。母亲从围裙的暗袋里掏出那十元钱,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中央。
“今天去镇上买点肉,给你们补补身子。”她说。
我们都愣住了。七弟的嘴巴张得老大,连红薯片都忘了嚼。
“娘,这钱不是要留着过年吗?”大哥问道。
母亲摇摇头,露出一个疲惫的笑容:“你们正在长身体,不能总吃这些。再说了,你爹要是知道你们这么辛苦,心里该有多难受。”
我看见母亲的手指在微微发抖。她低下头,继续给我们分红薯片,但这一次,每个人的碗里都多了一片。
去镇上的路上,大哥背着七弟,我和其他兄弟跟在后面。阳光很好,照得人暖洋洋的。路过王婶家的小卖部时,五哥又忍不住往橱窗里张望。
“等买了肉,剩下的钱给你们买糖。”大哥突然说。
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七弟在大哥背上扭来扭去,差点摔下来。
“真的吗?真的吗?”他不停地问。
大哥笑着点点头:“真的,一人一颗。”
镇上比村里热闹多了,到处都是人。肉铺前排着长队,我们等了好久才轮到。母亲仔细地挑了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,又跟老板讨价还价了半天。
买完肉,果然还剩了一些钱。我们站在小卖部门口,看着琳琅满目的糖果。五哥指着一颗红色的水果糖,眼睛亮晶晶的。
“要这个。”他说。
母亲给我们每人买了一颗糖。我小心地剥开糖纸,把糖果含在嘴里。甜味在舌尖化开,比想象中还要美妙。七弟吃得最快,眼巴巴地看着我们。
“慢点吃,”大哥说,“等过年的时候,说不定还能再吃一颗。”
回家的路上,我们轮流背着装肉的篮子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像一串歪歪扭扭的糖葫芦。母亲走在最后面,手里攥着剩下的糖纸。
那天晚上,我们吃到了久违的肉。母亲把肉切成薄片,和野菜一起炒了。香气飘满了整个屋子,连邻居家的狗都跑来门口转悠。
我躺在炕上,嘴里还残留着糖果的甜味。月光依旧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,但这一次,地上的光斑似乎比往常要明亮一些。
七弟在睡梦中咂了咂嘴,喃喃地说着梦话:“糖……真甜.……”
我闭上眼睛,感觉浑身的酸痛都减轻了不少。明天还要去捡麦穗,但想到嘴里残留的甜味,我觉得自己还能再捡很多很多。
母亲在灶房里收拾碗筷,我听见她在轻声哼着歌。那是一首很老的歌,讲的是春天的故事。歌声断断续续地,却格外温暖。
我知道,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很久。父亲的工资依然微薄,我们依然要省吃俭用。但至少在今天,我们尝到了甜味,尝到了希望。
月光静静地洒在炕上,照着我们七兄弟挤在一起的睡颜。在梦里,我看见了父亲回家的身影,他手里提着一个鼓鼓的布包,里面装满了糖果。
这个梦,比以往任何一个都要甜美。
(二)
我们那里有两个紧邻的大屋场,一个叫尿婆塘,一个叫操戈塘。尿婆塘大部分人姓徐,操戈塘大部分人姓舒。二个大屋场加起来约有85户村民400号人。每年大年三十晚有一个传统习俗,叫火龙接糖。就是小孩打着灯笼到各家各户去接糖,你家有几个孩子就给几粒糖,我家有七兄妹,所以每年接的糖就不少。约50个小孩打着灯笼,把两个大屋场照得灯火通明,一字排开就是一条长长的火龙,甚是壮观。
又是一个除夕夜,操戈塘和尿婆塘两个大屋场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。八十五户人家的屋檐下,早已挂起了红灯笼,暖黄的光晕在寒风中轻轻摇曳。暮色四合时,不知是谁家孩子第一个点亮了手中的灯笼,紧接着,星星点点的光亮次第亮起,像天上的星星落在了人间。
“接糖喽——”清脆的童音划破了夜的寂静。五十多个孩子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从各家各户涌出来:有红彤彤的鲤鱼灯,有圆滚滚的南瓜灯,还有精巧的莲花灯。我提着父亲亲手扎的兔子灯,牵着七弟的手,身后跟着其他三个弟妹。灯笼里的蜡烛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,在地上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。
队伍渐渐成形,孩子们自觉地排成一列。灯笼的光晕连成一片,远远望去,宛如一条蜿蜒的火龙。火光映红了孩子们的笑脸,照亮了青石板铺就的小路。走在最前面的孩子举着一盏特别大的龙灯,龙的眼睛是用红纸糊的,在夜色中炯炯有神。
每到一户人家,我们便齐声喊:“接糖喽!”主人家早已备好了糖果,笑眯眯地站在门口。按照规矩,家里有几个孩子就给几粒糖。七弟最小,总是把接到的糖果迫不及待地剥开糖纸,老五轻轻拍了他的手:“回家再吃。”他便噘着嘴,把糖果小心翼翼地放进母亲缝制的布袋里。
灯笼的光晕在青石板上跳跃,映得路边的腊梅花影婆娑。空气中飘着糖香和腊梅香,还有孩子们身上新棉袄的淡淡清香。队伍经过祠堂时,老族长拄着拐杖站在门口,看着这条火龙,眼里泛着泪光:“好,好啊,这传统要长久传下去。”
走到尿婆塘时,月亮已经升得老高。月光和灯笼的光交相辉映,将整个大屋场照得如同白昼。队伍经过池塘,水面倒映着点点灯火,仿佛天上人间连成了一片。有调皮的孩子故意摇晃灯笼,水中的光影便碎成一片金波,惹得大家哄笑。
夜深了,火龙渐渐分散。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往家走,灯笼的光晕在巷弄间忽明忽暗。回到家中,母亲早已备好了热腾腾的饺子。我们兄妹七人围坐在桌前,将布袋里的糖果倒在桌上,数着今晚的收获。七弟的糖果总是最少,因为他在路上偷偷吃了好几颗。老五便把自己的分给他一些,他立刻破涕为笑,露出缺了门牙的笑容。
屋外,零星的灯笼光还在闪烁。远处传来零星的爆竹声,预示着新年即将到来。父亲说,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上百年,从他爷爷的爷爷那辈就开始了。那时候没有电灯,火龙便是除夕夜最亮的光。如今虽然家家户户都有了电灯,但这个习俗却一直保留下来,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。
如今,每当我躺在床上,我仿佛听到窗外隐约的爆竹声,想着那条蜿蜒的火龙。灯笼的光晕仿佛还在眼前晃动,糖果的甜香似乎还萦绕在鼻尖。我知道,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接糖游戏,更是一种传承,一种乡愁,一种对团圆的期盼。在辞旧迎新的夜晚,火龙不仅照亮了两个大屋场的路,更照亮了每一个游子的归途,温暖了每一个思乡人的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