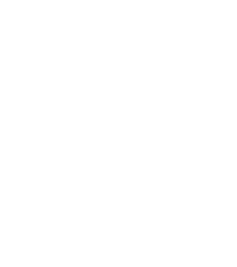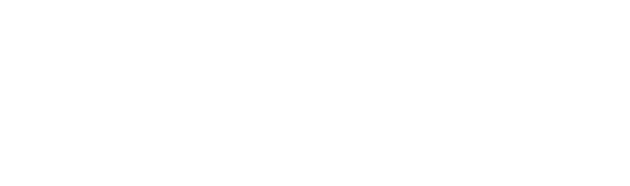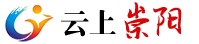作者:庞步高
阳春三月,我脚踏湿润的田埂,回到乡下老宅。推开朱漆褪去的院门,檐角忽地闪过一道剪影,清脆“唧啾”声洒落。仰头瞧去,去年斑驳的泥巢已修缮一新,两只黑身白腹的燕子正叼着草茎往来忙碌。母亲在廊下择菜,见我愣愣望着檐角,笑纹里满是旧时光的影子:“去年那窝燕子,到底还是回来了。”
记得儿时背诵唐诗《乌衣巷》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刘禹锡大概没见过江南的燕,我们这儿的燕子不栖华丽雕梁,独爱人间烟火。老宅五间正屋的青灰瓦当间,年年都能寻见三五个泥巢。春雷初响的清晨,乳燕的啁啾混着灶间粥香,唤醒整个院落。母亲晾晒蓝印花布时,常有雏燕错把布匹当晴空,扑扇着新羽一头扎进棉麻的“云朵”里。

暮春黄昏,最是难忘。我常踩着竹梯爬上廊柱,偷看巢中的雏燕。它们琥珀色的喙如同待放的玉兰苞,每当空中传来振翅声,七八张小嘴便整齐张开,露出嫩红的喉腔。成年燕子归巢瞬间,总能准确将飞虫投进某张开合的小嘴。父亲说这是燕子识数的本领,我却觉得它们心里藏着账本,每日清点每只雏燕的饥饱。

有一年梅雨季,我突发奇想,要做燕语译者。用黄草纸记下长短不同的“啾唧”,想用注音符号拼凑鸟言。直到一天暴雨如注,归燕浑身湿透仍往返喂食雏燕,翅膀拍打雨帘的声音比雷声还响。母亲把我从竹梯上抱下,指着檐下说:“你瞧,燕子教崽从不用嘴,扑棱翅膀就是上课。” 那一刻我忽然听懂,那些高低起伏的啁啾里,全是翅膀划破气流的声音。
我细看泥巢纹路,细草茎像纵横交错的小路,湿泥带着湖波的纹理,偶尔还嵌着半粒青瓦碎屑。它们秋去春归,穿越的不只是地理纬度,分明是把整个江南烟雨背在翅上。就像此刻檐下这对,或许曾在棕榈叶下避雨,在晨雾里啄过早露,却始终记得巢中每根稻草的模样。

暮色渐浓,新燕开始练习俯冲。它们掠过天井里的老柿树,翅尖扫落几朵白槐花。母亲倚着门框的身影被暮色勾勒成剪影,与檐下泥巢形成奇妙对称。我突然明白,燕子年复一年修补的不只是巢穴,更是为游子留存故乡的原点。每道衔泥轨迹,都是寄给天空的家书;每声呢喃燕语,都是未曾说出的归期。
瓦当上的青苔愈发厚实,燕巢边缘的草茎却始终鲜亮。这些空中的漂泊者用一生丈量归途,让所有离开都成为归来的起点。当春风再次吹皱故乡河水,我知道会有某只燕子穿越远方月色,翅膀凝着薄霜,却记得我家檐角第三片青瓦的温度。因为每个燕巢都是盖在屋梁上的邮戳,而游子,不过是将故乡穿在身上,岁岁往返的候鸟,无论飞得多远,故乡的方向,始终是心之所向。
(图片由AI生成)